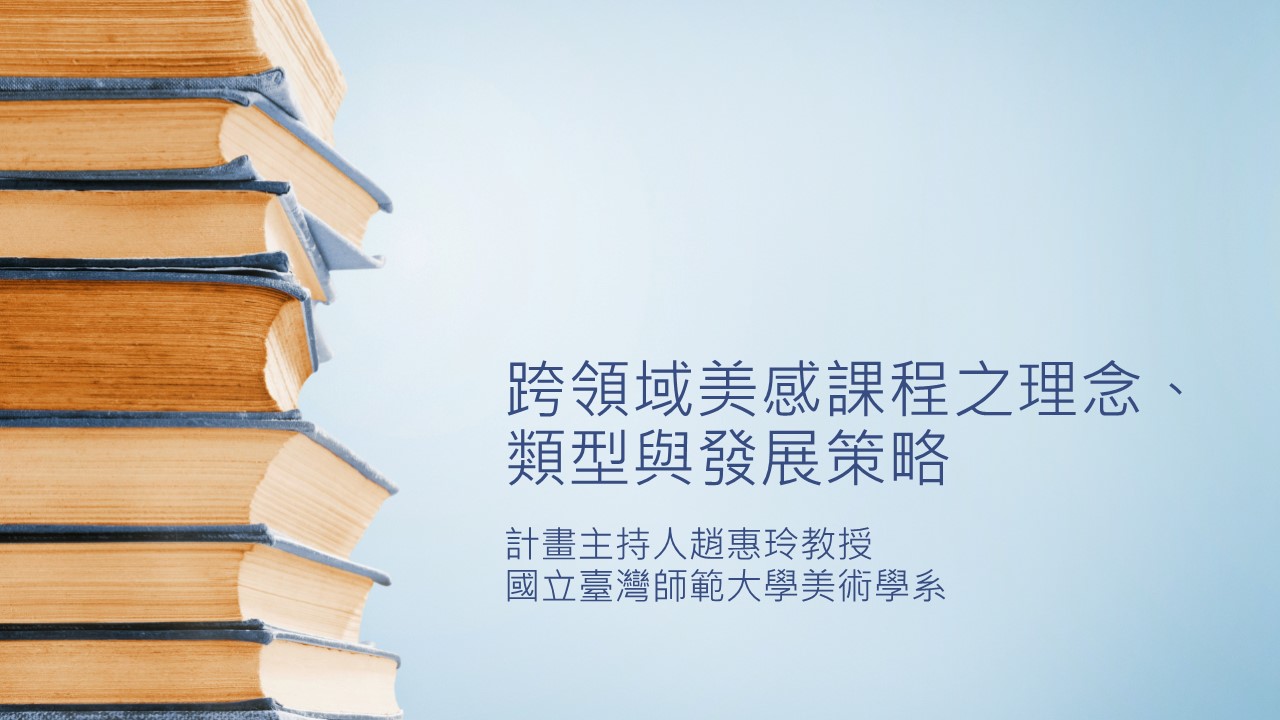從非藝術學科談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
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 鄧宗聖副教授
一、前言
當代藝術與非藝術學科之間關係密切,當畫家標誌「畫室就是實驗室」(Paint Lab),材料與概念是操作變項,自我與環境關聯則為依變項(Forman, 2013),可以看到藝術借用實驗的概念強調探索性。無獨有偶,有創作者會引用數學家Fibonacci提出的黃金比例概念於繪畫,之後延伸到媒體藝術;有創作者會引用瑞典Svenska Vaxter觀察植物形態的海報延伸出生態繪畫;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中主角扮演理論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s),除了研讀劇本外,還要能理解神經科學中運動神經元疾病的成因並揣摩發病過程,在表演中如何運用身體來表現。前述無論是數學或自然科學領域的成果,都轉變為生活世界的文化符碼成為創作者的靈感來源,而視覺與表演藝術家的創作能力則建構在理解過程,而非作品畫面、舞台或媒體作品上的結果。
不過,課程乃學校內結構不同學科與教師分工的客觀化實體,藝術與非藝術學科之間有時卻有競合關係,非藝術學科如何進行跨領域美感課程?其目的上究竟是「教導學生學習學科理論?」抑或是「透過學科進行藝術創作?」,這裡預設的既非學習學科理論,也不是用學科做藝術創作,而是強調藝術的跨領域特質,「讓藝術創作成為探索學科概念的角色」。這個預設目的如何可能?這裡先從自然科學領域談起。
二、從自然領域的跨科概念談起
當代教育反省科學學習的問題。在臺灣,自然領域課程綱要的制定受美國〈下一代科學標準〉(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以下簡稱NGSS)影響,對國內科學教師而言,新課綱與過去國民教育自然領域中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內容與精神新增「跨科概念」的實作,建立模型與系統性思考的科學素養。因此自然領域老師參照NGSS,要明確指出三種面向「核心想法」、「實作」、「跨科概念」形成評量準則(邱美虹,2016)。事實上,藝術創作也包含了前兩種面向,無論是表演、視覺或音樂都具有其核心特質與實作面向。
Wheatley(2007)曾例舉浪漫主義時期英國鄉村風景畫家John Constable核心概念是「想畫出風景的真實樣貌」,其在視覺藝術的實作就是「質疑達文西為風景畫研究的大氣透視的技法」,同時透過不斷寫生研究雲彩與天空變化而形成自己對透視法的新觀點;1850年攝影術發明,當初藝術家以為科技媒體會影響大家創作,但後來讓藝術家發現,反而不用擔心畫得像不像,還被鼓勵畫出想像的場景,像是象徵派畫家Odilon Redon其核心概念是使用視覺探索「表達情感與想法」,從自己的想像出發創造出神秘的景象,這些創作都是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東西,無論象徵裡的東西是人、物或是色彩,都代表特別的感受與意念;或是印象派畫家的核心概念是「紀錄色彩與光線」,無論是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或梵谷(Vincent van Gogh)其創作則是運用「用較粗大的筆觸實驗色彩理論理的對比色與色彩形狀」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想法;1900年立體主義邁向抽象主義,無論是馬諦斯(Henri Matisse)或馬列維基(Kazimir Malevich)其核心概念是「色彩與圖案就像是音樂一樣可以觸及人的感覺與意念」,創作表現上「色彩與圖案」兩種元素的應用。
從前述藝術史的角度來看,每一個藝術創作的誕生,幾乎都涉及到核心概念上核心概念的探索以及實作上的表現,單一畫家及其作品形式或情感理念表達的故事,都是一個環境與自我關係的關係對話與探索學習歷程,當仔細比較NGSS中的論述,前述藝術史中的創作群體,跟自然科學家都在做類似的探究與實作,不過發展於相異的文化社群,因此藝術與自然在使用學科概念時的語言本身就指向不同的場域。因此不需要擔心藝術與自然的核心概念與實作問題,反而是要問:如何在學習者身上引發本來就存在於核心概念與實作間的「連結」? 如此才能對非藝術學科在跨領域課程與美感的角色與定位。
NGSS倡議跨科概念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來自於自然科學之間溝通的語言問題,認為無論是理化、生命科學、地球與太空科學、工程、科技、應用科學等,彼此各科各一套語言模式與術語,彼此能夠相互溝通的原由來自於跨科概念之間的共同性。國內學者黃茂在與吳敏而(2016)解讀跨科概念的誕生,乃是活用自然科學知識而非記憶事實知識的主張,過去臺灣自然科學課程目標隱藏當代科學社群對自然科學教育的期待與價值與素養內涵的詮釋,因此本來臺灣自然科學課程目標是從模仿一個科學家的研究歷程(科學知識、研究方法、處理問題的態度),經歷重視個人學習方式多元性(科學概念由學習者主動建構),到新課綱裡呼應國際課程發展的跨科概念。就此來看,藝術領域與自然領域彼此在「概念由學習者主動建構」的學習多元之立場上彼此應可以相互溝通與理解,跨科概念應是為「學習者」發展自我探索的價值主張。
三、非藝術學科的困境與挑戰
過去教育裡常誤解「跨領域」的意涵,把「統整」當作一種「大單元」,教師用各學科來拆解它,以致於設計主題式的跨領域,比方說在生日的主題下,語文科就安排寫賀卡和邀請卡,數學科就安排計算年齡和採購禮物的算術活動,自然科學則安排生日派對汽球和空氣實驗。不過,前述乃「拼湊並非結合,因為領域之間的學習,並沒有相互獲得互動和互補」(黃茂在、吳敏而,2016)。由於學校、教科書等並非為課程統整而設立,教師們與學生合作協作都耗時耗力,加上科目間主副科的地位關係,同事間也不一定會分享權力(單文經,2001)。此外,過去教學現場只講觀念或用食譜式操作實驗,教師把考試會考的內容知識視為己任,不然會影響學生科學能力,但程序性知識探究卻毫無感覺,而且教師多使用教科書,提供知識量相當多卻難有時間進行探究實作(張嫈嫈2020),儘管總綱規定三分之一的時數進行,但是教師認為探索方式與快速教完科學概念所獲得的探索共識相近,可能因費時較長而感覺沒有效率。換言之,探索行動不只是學生個人自己操作,在教室內還要與同儕互動、討論與處理數據、分析歸納結論並做共識分享。就此來看,非藝術學科需要面對不僅是表面上合作的誤用,如何在實作內產生探索也是一個挑戰。
為了避免這樣將跨科視為主題式的操作與誤用,非藝術學科的跨領域美感課程究竟樣貌為何?Wiggins與McTighe(2008)引用腦科學的實證研究,主張課程是「重視理解的設計」,或許理解本身定義不嚴謹,其意義就是多面向的,但其本身存在的直觀,更強調不同於「精熟內容」。據此,我們應將跨領域中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相互理解當作依變項,非藝術學科實踐跨領域美感在學習的意義上並不是「知道多少」,而是「如何理解」的歷程。
非藝術學科要跨越的障礙,除了學科分工的學術傳統,就像是國內教科書或相關教案編撰本身,也未使用其他領域的語言,自然領域不會使用藝術領域語言結構在自己的文本。換言之,只要跨越領域語言的習慣,藝術領域與自然領域在概念上應是可相互為用。對藝術創作來說,原本食譜樣態「原理實驗」是可以透過「創作」來加以反思的文本,使用其觀念作改造設計,如此自然科裡材料包實驗也不會流於食譜操作,而是在創作中轉化成探索內容則如前述NGSS所提跨科概念是學科間能相互理解的語言。
四、用藝術創作來探索非藝術學科的概念
Wiggins與 McTighe(2008)認為「理解」本身就是一種概念,它來自分析並反省我們的學習,從過去片段或難以了解的學習產生有意義的通則、洞見或是有用的了解,理解不是事實知識,而是一種推論結果,由學生發展及驗證,但必要時由老師幫助獲得的概念。據此,藝術,在這裡應被理解為「儲存概念的形式」最為首要。換言之,藝術形式既是學習內容也是學習的表現,像是美術在談論構圖的時候,有哪些好的構圖既是創作者思考表達的形式,如何思考構圖亦是創作者學習表現的內容。它們不需要被說出來,只有當藝術結合到自然領域、社會領域、生活領域等概念裡時,透過「探索」變身為學習者談論「我如何使用」時的故事才值得一說。
國內學者歐用生(2003)就強調使用「學習領域」一詞,就是要從傳統學科裡學科內嚴謹牢固的價值學科文化中解放出來,因為學科文化形塑了教師主體,不僅代表課程、教科書與測驗的內容,更代表教師的身分、地位與權威,因此把教師侷限在自己的社群裡效忠,較少有機會在這過程中交流。他因此強調要重視影像文本,相對於狹義的教科書而言,各種媒介形式的口語或書寫敘說,都是讓學生去與某種隱含要與文本的客觀化知識對話,藉由這種觀點擴充課程的意義,文化產品與人工器物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蘇格拉底。
前述「藝術作為儲存概念的形式」的樣貌,這裡以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資料庫的南投市漳興國小為例,該校以表演藝術作為儲存概念的形式,將繪本《家在山那邊》當作引發的媒介,主要的內容是土石流災難的成因與影響為概念,連結到自然科學裡的植物與山林。這裡有趣的問題就出來了,在教室裡,國小學生如何理解無法直接目睹的事物(土石流)?《家在山那邊》的故事作為替代性的模擬經驗,故事裡透過漂流木的「獨白」,說出土石流災害的影響,於是從種子到土壤、雨水循環、植物涵養土地等「事實性知識」敘說出來,這樣的作法除了閱讀繪本外,還針對其情節中提到「巨人的大梳子」(減緩土石流災害)的製作與觀察,模擬參與了這場演示,然後再透過表演藝術演出這些自己的觀察。
非藝術學科的教師若能把跨領域教學當作一個創作品,把教學當作藝術、自己就是藝術家,而藝術家本身不是傳統意義下的精熟媒材的創作者,而是在教學是藝術的意義下,扮演探索的連接號,非藝術學科的藝術家則是走在連接號上觀察、思考、耕耘與反省的人(吳麗君,2010)。林逢祺(2010)更直指教學本身是遊戲的結構,具有放鬆的特質,那是在課前一種感性知覺與理性思維的飽滿精神狀態,但不以課前準備充分作為教學內容之主體,而是不斷要求適時把學生的感覺與思維邀請近來豐富課堂中的感性與知性的材料,樂於根據學生的貢獻修正課前預訂傳授形式與法則,這樣的教學才有冒險的意義,共同開拓園地時刻的探究歷程。
非藝術學科的跨領域課程就是「直接從事一個創作」,而不是固守於精熟各學科的內容,教學不應該看作是知識的傳遞行為,而是雙向溝通的轉變,創作作品就是一種溝通媒介,鼓勵學生如當代藝術家般地發揮潛能與創作。這裡建議,非藝術學科老師皆可直接擬訂一個創作活動,學生可以參與創作活動的提案與設計、只要能對問題有所感受、反思想要的改變,就能開啟不同學科間的對話空間(楊忠斌、林素卿,2010)。 因此這裡特別關心,非藝術學科教師能想像在結束課程後想說:讓我來說一個關於我如何用X概念創作的故事。這或許是非藝術學科從事跨領域美感須具備的起始語,教師讓學生有願望去使用這些概念並克服困難,而不是如前述在主題大單元中的貌合神離,而是意外地發現自己的創作緊密鑲嵌在不同學科概念與語言。
五、非藝術學科的創作課程設計
Erickson, Lanning & French(2017)以概念為本的單元設計,採取三個維度去思考創作歷程的結構進行藝術創作轉化為跨科概念,包括什麼(單元標題或焦點)、為什麼(為了瞭解……接受評量的單元通則)以及如何(學生評量任務的敘述)。以Darbyshire(2016)的作品為例,她把人體內部視為一種「奇觀」,許多人談的美是外表而非內在,因此她嘗試使用顯微鏡放大細胞,從對稱性看到美感。這裡把這個藝術實踐轉化成跨科探究的創作課程時,其可解構為自然領域裡的形態與藝術領域裡的視覺構成,用三個維度來轉化:
- 什麼:顯微鏡下細胞的型態與結構(焦點)
- 為什麼:為了瞭解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探索裡面各種形狀與樣態等視覺元素。(跨科概念)
- 做什麼:用你覺得美的顏色與方式,創作出一幅風景畫,表現你覺得的內在美。 (創作歷程)
同樣的,教師慣用的教科書文本也可以作改編,以小學三年級上學期自然領域一「植物的身體」為例,教科書裡三組活動包括認識「根莖葉」、「花、果實與種子」、「植物的功用」可以結合眼觀、鼻聞、觸摸等觀察行為,不僅記錄樣態也記下接觸的感覺。這些在教室裡本來可以看著課本圖片講授的單元,在校園裡面轉化成一組探索活動。但我們如何把自然領域的文本與藝術領域的文本融合?對照三上同一時期的教科書,藝術領域以「家」為出發點,加入創意與夢想的想像力,那麼一個單元中原本三節的自然課與兩節的藝術課,在評量與習作的結果轉換為藝術本位形式,亦即「創作歷程」。
那麼藝術老師與自然老師可以討論如何合作,並用作品來評量,將學生探索植物的過程,變成一個創作品。自然與科技不是寫出認知面的事實,藝術領域對於創作出夢想之家,因植物構造有些新的元素,譬如說:「假如我住進花裡當我的家,要怎麼擺設設計」之類。當然探索行為的習作,可以是一種想像力的奔馳,嘗試放大空間區位,像是把觀察放到:「回家路上」當作一個冒險地圖,讓學生把動作放慢,觀察放得更加敏銳,在回家的路徑上,發現週遭的自然物質,無論是花草樹木,賦予其模特兒般的角色,把自身常做的動作與對話放在葉子的身上作表演,利用葉子外型輪廓與內在的葉脈紋路作一個「回家冒險地圖裡的表情包」,於是這個視覺藝術,同時具表演形式。如前所述,藝術創作轉化成探索科學概念的學習行為時,也可以善加沿用教科書裡的素材加以變形使用,用三個維度來轉化:
- 什麼:從家到學校路上的植物的「形態」(焦點)
- 為什麼:為了瞭解這些花草樹木的型態與結構,把這些當作家人介紹,使用這些外型輪廓特徵,建構出家人常用的台詞與表情。(跨科概念)
- 做什麼:回家路上的冒險地圖並創作出的家人的表情包。(創作歷程)
把視覺形式換個音樂形式可以嗎?是否一樣可以做溝通?Humphreys把現象看似聲音與音響品質的再現,在藝術活動中體會出獨特且多變的經驗,在這表達裡面有批判性的思考(王瑞菁譯,2007)。在此理念下,同樣可以把上述「回家路上」的案例轉化為音樂形態的表演,藉由簡單的身體律動,包括拍手、跺腳、彈手指創造出一些簡單的樂句:
- 什麼:從家到學校路上的植物的「形態」(焦點)
- 為什麼:為了瞭解這些花草樹木的型態與結構,加上身體律動描繪外型輪廓,跟著旋律建立起表情系列樂句,想像並為它配上適合的節奏。(跨科概念)
- 做什麼:為回家路上編織一支舞蹈。(創作歷程)
六、藝術與非藝術學科的二象
我們可以把「美」視為一種客體來研究,精確量測關於它的相關物理資訊,數值化美的設定,但物理資訊與數值的複製品,真的就是美? 這裡面有許多有趣的問題可以討論,在文末則要聚焦在觀察者,以打破藝術與非藝術學科的界線。
量子力學裡有一個知名的實驗叫做「波粒二象性」,觀察的對象是「光」,但光是粒子還是波?就與觀察者有關。當觀察者假設光是粒子時,就會將注意力放在粒子的現象;當假設光是波時,就看到波的流動,但事實上兩者都存在,這也說明無論如何客觀的觀察,觀察者的假設已經決定優先觀察的對象。這裡引申把藝術學科想成可被觀察的粒子,把非藝術學科看成是一種波,因此在跨領域課程中如何認識自己對世界的假設,持有的觀點與價值觀,是創作行為中重要的課題。據此來看,畢卡索的《格爾尼卡》、《貓吃鳥》、《納骨堂》等藝術創作是粒子,戰爭、屠殺與人權的社會學科就是波;車諾比兒童的詩與畫作出版成《想要活下去—車諾比孩子們的吶喊》是粒子,那麼面對災難與生命重建的人文學科就是波。
Lupton與Bost(2008)從設計觀點來看,想跟誰說?說些什麼?這些會決定計畫是否能產生有效的溝通。任何一個事件對人的心靈會產生衝擊,而事件在不同人的心靈世界裡,會在不同學科引導下耕耘形成知識景觀,而藝術創作也是在知識學科的分野下產生探索行動,以表現對事件關切的情感。這裡認為,在生活事件觸發下知識世界的分歧,卻在心靈聯繫中產生關聯。各類非藝術學科透過藝術化的歷程提供源源不絕的創作材料:科幻懸疑電影裡把科技與心理分析產生交集,自然生態變成引發人文心靈的觸媒,設計裡把成本、永續、公共綠地、回收減廢、能源危機等轉變為創作任務。
各學科會去發明或編造成為學科的條件,產生藝術與非藝術學科的邊界,但從敘說觀點來看,非藝術學科提供解釋這世界面貌的多元版本,每一種學科視野都決定世界意義的多重存在。
雖然許多非藝術學科的知識凌駕藝術表現,其中學科專家又常以上帝之聲的方式出現,但不難理解物理學、感光與攝影科技的知識支持攝影藝術家的誕生,在《Animal Beauty》也可以看到藝術家細膩的觀察不亞於動物學家,在《Hidden Lives of Works of Art》的紀錄片中彰顯科學協助藝術修復的夥伴角色。食物從土壤到智作過程中的展示,記錄人與環境科學的緊密關係,如《Science and Wine》把食物生產方式中的文明作了科學式的解釋。在《I post Therefor I Exist》紀錄片中把按讚、貼照片的人類行為與文化現象連結社會心理學的討論。Stephen Hawkings也會使用科幻電影裡想像力的情節,來談科學觀念與當前科技研究的執行力。
非藝術學科與藝術學科之間的連結,猶如我們對事物的動靜感受,有時心無旁騖時,即便結廬在人境也會有無車馬喧的寧靜,有些事物微小與緩慢的變化卻不一定能覺察。物理學上空氣的概念是實體,看不見它卻在流動,唯有關照呼吸時才能感受它的存在。一般來說,非藝術學科可以將各種「已知」的概念當作重新加工的材料,像是打哈欠表情當作一種生物觀察的題材、統計在一小時內有多少時間打哈欠?是否改變空氣中氧或二氧化碳濃度?不同物種打哈欠時候的行為是否有地位或是示威?用醫學來解釋是否關係到新陳代謝、清除與燃燒、能量;用生物學來解釋,是否關係到大腦或遺傳進化?這些引用科學術語,加上計量表徵與意義賦予,然後看起來似乎就是一種引用某種假設(探索概念)或解釋方式(實驗室或生物觀察)的創作。
因此非藝術學科若能媒體環境中的各種設計做解讀與改善,也可以跳脫教科書的綱要與進度的限制並加入當代議題。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曾展示一張漢堡圖像為例,這張漢堡圖像一分為二,左邊顯示牛與排碳量的資訊搭配龜裂的地表(代表乾旱),右邊則是盛滿蔬菜的圖案搭配均質的綠地(代表自然),斗大標題寫著「跳過漢堡」(skip that burger)暗示消費者食物的選擇與碳足跡有關,消選選擇與永續生態的因果關係。想像有人要點餐,那麼海報創作裡的場景與文字細節可能會讓人感到不安與猶豫,除非刻意忽略,海報設計更連結到選擇食物與環境保護倫理有所關聯。
若我們將此氣候變遷議題的海報設計做拆解,當作非藝術學科的探索路徑,那麼漢堡圖像可以疊加曼陀羅思考的九宮格表,取用其中左右三格、左右對稱呈現對立的訊息,再取用中間上下兩格選擇相似訊息,將其轉譯為圖像後變成一組具有議題概念設計的海報原則,把科學知識置入在藝術創作中思考,再加上創作論述就能有更精確的理解。在此案例中,漢堡以碳排概念作為重新「造像」的依據,真實照片附加學科概念作為跨領域對話的舞台。當然也可以根據氣候變遷的成因與影響,利用先前科學原理與災害的資料,去想像模擬滅亡的劇本,如大洪水、二氧化碳過多金星化、回到冰河時期凍結、臭氧層破壞後的生態浩劫、宇宙外圍隕石灰塵等衝撞地球的威脅。當引用氣候科學的各種可能推論,在死亡想像的劇本安排下,非藝術學科的藝術化形象能促發對環境改善的參與。
如前述,氣候當作跨領域的場域來看,其實既然形成氣候的條件是水與溫度,那麼我們可以發揮想像力把水與溫度交會的地方都當作一種氣候狀態,只是它不是發生在地球,但我們卻可以用假設,去創造所謂的微氣候,這時候這咖啡杯不就是藝術的材料了?喝杯咖啡時,咖啡杯上面的雲霧繚繞,攪拌時候的力造成的風暴,溫度熱氣帶來的白菸,冷熱交錯下黑白相間的顏色與區域等等,就可以觀察到,談著各種觀察與感受,雖說不出科學的力,但也形成了感受之美的寫照。
柒、小結
物理學家Hawkings(2020)曾自述自己動手做的能力跟不上思索理論的能力,理論就是宇宙運作的原理,他強調多數人需要的「觀念」科學,而不是定量與複雜的方程式。觀念在定性上的說明提供好的理解,像是科學裡提出的問題都是人類生活相關,包括全球暖化、搶救瀕危物種、發展新能源、阻止汙染與資源濫用、防止傳染病等,依賴科學與科技也變成日常生活中待解決問題的清單之一,各種發明與創新也都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溝通等日常型態。
在眾多非藝術學科的概念應用在跨領域美感教育時,我們則要問:在這麼多的詮釋版本中,究竟是什麼因素決定了某種特殊版本,又那些版本能在非藝術學科的課堂裡勝出,成為所經歷過的學習經驗?就跟任何藝術創作一樣,確實需要動機或說動力源,尋找存在意義有關。我想,把任何課程比喻為師生回憶的「時光膠囊」或是「瓶中信」,只是用創作而非考試的方式存在。當這份以創作為名的書寫或相關作品完成後,把它放進我們記憶與經驗裡的倉儲後,就好像把它丟進浩瀚的宇宙或大海,等待一個安排已久卻又未知的境遇。這份精神性禮物的命題,讓感覺的能量充沛,好像是某個使命與不可言喻的力量在召喚我們這麼做。
非藝術性學科是一個抽象的命題,但若過度集中在這個詞義的解釋上又會顯得繁瑣而失去寫作與閱讀的趣味。我建議可以理解成一種「表演」,任何創作者展示作品時,都會有「能說的」與「想說的」:能說的是一種我們都可以理解的文字,但想說的不一定說得出來,得借用文字或語言以外,也就是作品本身去闡述,而想說的一部分也會是欣賞者與創作者的共同跳舞,我在解釋的時候就是那個欣賞者,在我的理解與詮釋中捕捉這一個對話感受。
藝術領域關乎的是符碼訊號,符碼訊號可以不只是語言的型態,所溝通的是個人的心靈,用物理學用語加以創造一種意象的話,它可以是一種頻率、振福,現在腦波儀或眼動儀等生理訊號偵測都可以測得這樣的訊號,我們在使用某種訊號、發出或接收某種訊號的時候,我們在數值儀表板上是有一種存在方式,而我用物理的方式確實也創造出這樣的心象,來解釋一種心靈在我們自覺好或壞、開心或沉悶、放鬆或緊繃的時候狀態,於是物理學的用法作為此種圖像的解釋時,某種波形或設定好反映某種數值的色彩就變成一種視覺訊號,對創作者而言,它也可以用來組織成一系列的作品,當作討論某種議題的題材。
符碼訊號在形式上變態過程,恰恰就是一種在「名為某物」卻「實非某物」的灰色地帶,一個作品可能是基於科學但卻用於藝術的創作,又或是某種基於藝術但卻用於科學的作品,我可以無止盡地這樣造句下去,延伸我們對各種想法交會可能性的討論,這些東西都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相遇,成為一種我們反思生活與存在的一種方式。看起來有理解這一點並不容易,就像我剛剛想談的是心靈狀態,但是卻用了物理的語言做了藝術的表現。同樣的,我採取的觀察策略則是這種引用的特徵,也將是貫串在這非藝術學科跨領域美感課程的書寫。